刘后滨:《唐朝政令如何落实到乡里 ——基层政务与国家制度的弹性对接》,《人民论坛》
上传时间:2020-05-2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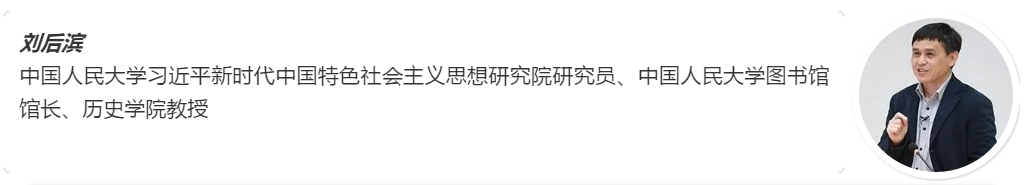
【摘要】唐朝前期国家治理体制主体是通过尚书六部和州县乡里实现中央集权的一套行政体系,运行程序贯穿着自上而下的决策执行机制,基础是虚实结合的基层行政单位乡里和村坊。律令格式对政务申报裁决机制有着详密规定,以保障朝廷政令逐级传达到基层,基层行政节级统属于朝廷。
【关键词】唐朝 基层政务 国家制度 弹性对接
自从秦始皇统一中国推行郡县制以后,中国古代帝制国家的治理模式就是中央集权、政令统一。为了保证朝廷政令顺畅地传达到基层,需要建立起完备的基层行政组织,完善运行机制。从总体发展趋势上看,秦汉以降,郡对县、县对基层政务的介入在不断强化,县级官府承担的政务无论从制度概念还是治理实践上都不断被细分,基层社会的治理任务在不变之中不断更新和细化,治理结构随之日渐完善。到唐代则达到了一个历史时段的整合,基层政务运行的制度化水平进入到一个新的阶段,基层政务运行机制较好实现了与国家整体制度的弹性对接。 唐代前期是所谓律令制国家,即国家的基本制度和政务运行细则,都是通过先后完善起来的律、令、格、式等法令条文加以规定的,实现了各项制度规定的高度法典化。唐《户令》规定(据《通典》卷三《食货三·乡党》引大唐令):“诸户以百户为里,五里为乡,四家为邻,五家为保。每里置正一人(原注:若山谷阻远,地远人稀之处,听随便量置),掌按比户口,课植农桑,检察非违,催驱赋役。在邑居者为坊,别置正一人,掌坊门管钥,督察奸非。并免其课役。在田野者为村,别置正一人。其村满百家,增置一人,掌同坊正。其村如[不]满十家者,隶入大村,不需别置村正。” 这条被称为“里”即关于里的建置的令文,并非法令具文,而是唐朝建国以后制定的至少一直行用到开元时期的基本制度,核心内容是按照户数来设立乡、里,百户为里,五里为乡,则一乡的户数是五百户。《旧唐书·玄宗纪》中记载了天宝元年(742)的州县乡数及户部掌握的户口数:“其年,天下郡府三百六十二,县一千五百二十八,乡一万六千八百二十九。户部进计帐,今年管户八百五十二万五千七百六十三,口四千八百九十万九千八百。”平均每乡约507户。又载天宝十三载(754)的统计资料,其中郡府略有减少、县数则稍微增加,但变化不大,而乡的统计数字与十三年前相同,依然是一万六千八百二十九,但是全国的户数却已经达到了九百六十一万九千二百五十四,平均每乡约571户,比天宝元年有了明显增长。这两年的统计数字说明,以五百户为一乡,按照国家掌握的户口数(即申报户口)来说是落实了的制度规定。 邻、保则是一种网格化管理的单位,每五户为一个保,其中任何一户都以其余四户为邻。设立邻保的目的是为了赋税徭役征派及治安管理中的责任连带追究。原则上每里置里正一人,其职责是“按比户口,课植农桑,检察非违,催驱赋役”,核心是催驱赋役,说明里正处于国家政务运行中的行政末梢,是为国家行政服务的。从乡、里的设置原则和里正的职责规定来看,乡、里是依附于县级政府部门(唐代称为县司)的基层行政单位,乡、里本身并没有自身的办事机构,只是对接县司下派的各项政务,而且主要是到县司去办理。整齐划一的以百户为里,五里为乡,制度的人为设计色彩十分明显,具有很强的构拟性,自然形成的聚落一定不会如此整齐。但是,大体以五百户为一乡,户口统计、土地调配和赋役征派以乡为单位而不是以里为单位。在乡的地域范围内,划分出五个里,里与作为聚落的村无法整齐对应,但是乡则有可能囊括若干完整的村。所以,乡才是政务运行中实际存在的基层单位,里则是将一个乡一分为五的虚拟单位。 已有研究成果显示,乡、里的运行方式大体是每乡五个里正轮流到县衙值班,由县衙进行点名,并由官厨提供饮食。如果是县司编造户籍、退田授田文书和差科簿等簿籍文书的集中工作期间,五个里正可能都要到县司当值。从吐鲁番出土唐前期高昌县的值班点名性质的档案看,在集中勘造簿籍的时间段里一个乡的多个里正是同时上值的。 前引令文在有关乡、里设置及里正职掌之后,接着是有关坊和村设置的规定,分别针对城邑和田野的居民,在邑居者为坊,在田野者为村,坊和村是“乡—里”之外的另一个系统。相对于乡、里作为构拟性的行政系统而言,村是一种自然形成的聚落,大小不一,坊则是在城邑规划出来的聚落。盛唐田园诗人孟浩然《过故人庄》的诗句“绿树村边合,青山郭外斜”,提示唐代的村庄大部分散布于城郭周边。通过对方志、族谱等地方史料分析,大抵从唐代中后期开始,村大量向城郭以外扩张,晚唐五代以后这种趋势在南方山林地区更加明显。 以上对于基层“行政组织”建置的规定,放在唐代法令体系中的《户令》而不是《职员令》之中,说明在唐代国家治理的理念中,乡里组织并不是国家行政体系中的一级,其中承担具体事务的人员也不是国家官僚体系中的职员,他们服务于国家政务运行中乡里事务的处理,其运行成本并不调动国家的财政资源。 里正和村正作为国家政权在基层的代理人,他们之间以及他们与其他社会力量之间的分工协作,是皇权国家实现行政系统与基层社会有效衔接的重要机制。基层的社会力量包括自发形成的“社邑”组织和得到官府认可的民间领袖。唐初王梵志的诗歌:“遥看世间人,村坊安社邑。一家有生死,合村相就泣。”描写的就是社邑这种在祭祀、丧葬以及其它生产活动和日常生活中发挥互助功能的民间自发组织。唐代的民间领袖,包括“乡望”和“耆老”两类身份,作为沟通官民的纽带力量,既得到官府认可,又具有民意基础,他们在基层行使教化及组织一些公共事务,也参加州县官府举办的各种礼仪活动。各种社邑和民间领袖与“乡—里”和“乡—村”二元结构的基层行政系统相辅相成,使得唐代的基层社会呈现出多层次的立体化结构。 唐代国家治理体制是由通过尚书六部和州县乡里实现中央集权的一套行政体系构建起来的,运行程序贯穿着自上而下的决策执行机制,构拟性的基层行政单位乡里及其基础村坊作为县级行政的延伸层面,由政府选补的行政代理人里正和村正执行县级官府的基础行政职能。国家政务从朝廷到乡村实现一体化运行,律令格式对政务申报裁决机制有着详密规定。 唐代国家政务运行通过严格的文书制度,由上而下的命令文书(含裁决文书)和由下而上的申奏文书构成了政务文书的主体,按照发文主体和行用范围区分为不同名目的文书,各有其规范的体式。《唐六典》卷一《尚书都省》概括下行文书的类别为:“凡上之所以逮下,其制有六,曰制、敕、册、令、教、符(注:天子曰制、曰敕、曰册,皇太子曰令,亲王、公主曰教。尚书省下于州,州下于县,县下于乡,皆曰符)。”皇帝、皇太子和亲王、公主都有自己的专用命令文书,行用于不同的场合和范围。 唐代国家政务机构的主体是尚书六部、州(含都督府、都护府)、县三个行政层级,在君主通过宰相协助实行高度中央集权的体制下,绝大部分政务的申报和裁决都要用皇帝的名义,包括皇帝下发制、敕,用敕旨批复奏状,以及在尚书省处理常规政务时制作申报上来的奏抄上御笔画“闻”等,可以概称之为制敕和御画奏抄。“符”是尚书省以下包括州、县各级官府转发皇帝命令文书(特殊情况如太子监国、亲王公主在其封国封邑内行使命令权)的公文,其所转发的文书包括作为皇帝命令的制敕文书和御画奏抄,以及皇帝用敕旨批复的各级官员申报政务的奏状。唐代政务文书中有一类是各级官员向朝廷提出的建议,称为奏状,由宰相审议后,皇帝用称为“敕旨”的命令文书批复,批准的一般格式是“敕旨:宜依”,即依照这个意见执行。 唐代政务运行普遍行用纸本文书,政务文书有规范的存档制度,但鲜有留存至今者。幸运的是吐鲁番出土文书中保留了一些具有档案性质的政务文书,其中有一些是唐代设立在当地的行政机构西州都督府下发至其所属各县(辖高昌﹑柳中﹑交河﹑蒲昌﹑天山五县)以及高昌等县下发至所属各乡的“符”。里正轮流在县司当值者,负责代表当乡接受县司下发到乡的“符”,其实也就是接受朝廷颁下的制敕,他们被称为“承符里正”。目前所见到的这些符,基本分为两类,一类是转发皇帝制敕文书的符,另外一类是转发经过皇帝敕旨批复的奏状的符。 第一类的例子可举《唐贞观二十二年(648)安西都护府承敕下交河县符为处分三卫犯私罪纳课违番事》(见唐长孺主编《吐鲁番出土文书》第七册)。此件政务文书的案卷,保存了从皇帝发出命令到交河县县司具体执行的行政全过程。其中尚书省签署后下发到都护府的用语是“奉敕旨连写如右。牒至准敕者,府宜准敕。符到奉行”。唐前期中枢决策和政务运行实行“三省制”,在中书、门下两省的起草和审核环节完成之后,制敕文书到了尚书省才能正式“付外施行”,尚书省将制敕文书转发到中央和地方行政部门,行用的是“符”,制度上称为“省符”,即“尚书省下于州”的符。都护府收到“省符”后再转而下发至交河县,转发用语是“交河县主者。被符奉敕旨连写如右。牒至准敕者,县宜准敕。符到奉行”。意思是接收到尚书省转发敕旨的“省符”,接着省符及与其连写在一起的敕旨再粘连新纸,写上给下属各县的转发用语“牒至准敕者,县宜准敕。符到奉行”。这是州(都护府)下于县的符。出土文书显示,交河县收到都护府的符之后,按照敕旨的要求具体落实。公文处理结束后,留在当处存档。 第二类的例子可举《唐景龙三年(709)尚书比部符》(录文可参考池田温《中国古代籍帐研究》)。当年,一些地方官员向皇帝呈状,建议停止追缴百姓拖欠的往年税赋,唐中宗批复同意,并下令将其出付朝廷政务部门商量,有关官员达成了一份提出具体实施意见的商量状,并上于皇帝,中宗对这份“敕后商量状”再次进行批复,然后经过三省出令程序,由尚书省负责向各州府下发,具体由尚书刑部的比部司签署,这就是比部符。文书中“牒奉者:今以状下,州宜准状。符到奉行”, 是尚书省诸司行符的标准用语。表面看来,尚书符转发的文件是“状”,但这是经过皇帝批准的奏状,否则不可能下发各州府执行。今见唐代文书中类似的用语,似都应理解为州县转发朝廷政务文书(即用敕旨批复了的奏状)的符,而不是州县处理自身细小事务的文书(此类文书一般用“帖”)。如吐鲁番出土唐永淳元年(682)西州高昌县下太平乡符,是高昌县下发给太平乡落实按照户等贮粮的要求,文书中有“太平乡主者。……今以状下,乡宜准状。符到奉行”字样,就是县司给各乡转发西州都督府的符,而西州都督府的符当是转发尚书户部的“省符”,如同景龙三年(709)尚书比部符一样。 从以上两种类型的“符”可以看出唐代行政的层级划分,也可知大部分政务都是中央直贯地方和基层。到唐代中后期,由于地方普遍设立了节度、观察使(唐人称之为方镇),在政务运行中增加了一个层级。所以白居易《策林·人之困穷由君之奢欲》一文中说,“君之命行于左右,左右颁于方镇,方镇布于州牧,州牧达于县宰,县宰下于乡吏,乡吏传于村胥,然后至于人”,形象地勾画出唐代中枢政令下达到基层的行政流程。而作为乡吏的“里正”,以其介于官与民之间的行政末梢之职任,其所承担行政事务的处理,在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上便与国家政务有效对接起来。 综括言之,唐朝的制度设计中具有完备的体制机制,以保障朝廷政令逐级传达到基层,基层行政节级统属于朝廷。但是,各级官僚及其机构的自利化取向,势必导致制度运行过程中的各种滞碍,包括信息的过滤与筛选。因此,唐朝还差遣官员或派出使职到地方和基层进行监督落实,构建起直贯基层的中央行政监察体系,以实现对行政阻滞的突破。“设官以经之,置使以纬之”,经纬交织,基层政务与国家制度的对接才得以基本实现。




